一
疫情突然来袭。春节前,我对疫情还没什么概念,安排好工作,然后,开始整理办公室,收拾行李,买了些年货,准备回海口过年。
23日晚上的飞机回海口。本来,我对传说中的疫情是不以为然的,也没戴过口罩。但妻子不放心,反复打电话,让我在飞机上要戴口罩。我想准备比不准备好吧,就在行李里塞了几个口罩。说句老实话,我以前对这一些都不以为然,非典的时候,我在海南,海南以安全岛著称,我对非典没有什么概念,非典期间还开车去三亚玩,虽然三亚的街头空空荡荡的。也没戴过口罩。后来到了北京,雾霾最严重的那几年,有时出门看不见对面的楼房,我也没戴口罩,觉得生死由命,坦然面对吧。所以,我没戴口罩就坐车去机场,专车司机已开始戴口罩了。上了飞机,才发现已是几乎人人都戴口罩,我也戴上,但感觉不适,在飞机上一会就摘下来,不时露出鼻子。我是一个自由惯了的人,觉得戴口罩还是很别扭。但尽量戴着吧。我后座的人咳得很厉害,好在飞机上人不多,我换到前面去了。其实这时已经能感到某种危险了。春节期间,北京到海南的航班从来人满为患,但现在竟然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人。
回到海口,各种消息越传越厉害,我感觉事情不会如原来想的简单,原来的一些安排就让先搁下了。我安心读书,足不出户。春节前刚和回国的田晓菲和她的责任编辑见了一面,得到好几本她的书,包括《留白》、《萨福》和《赭城》,我都带回来了,就开始陆续看。因为每天生活很有规律,而且也没有出门的打算,几个要来拜年的亲戚朋友也被我劝止了,所以,看书的速度很快,看书让人远离现实。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总觉得这个事情不会耽搁太久,上次非典不是很快就过去了吗?但微信圈里,朋友们的焦虑感持续扩大。尤其武汉不断传出各种不好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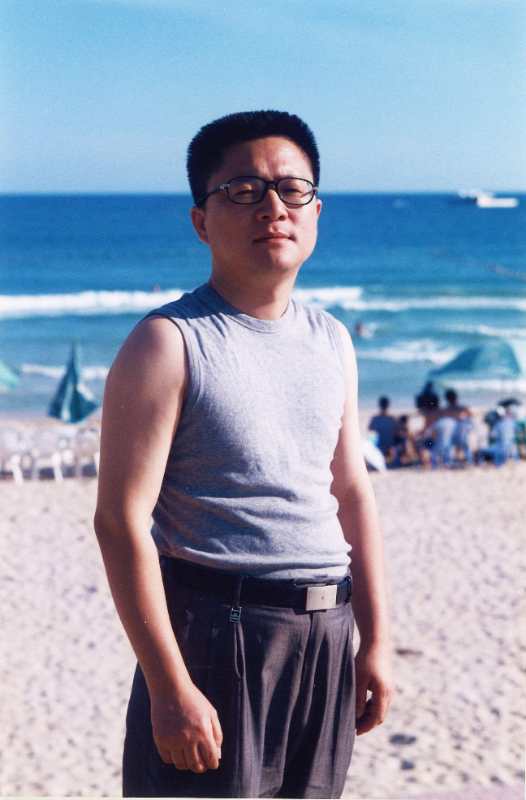
刚上岛时的李少君
因为以前在武汉大学读书,武汉的诗人朋友比较多。我对武汉格外关注,和武汉的诗友们一直保持联系。到了大年初二,我突然想,诗人们还写诗吗?我自己心情纷乱,没法安心写诗,但如果武汉的诗人们写诗,起码传递出某种信息吧,证明即使在重大灾难之中,人还保持着某种精神。于是,我一个一个去联系,准备在诗刊微信号上推出“武汉诗人系列”。联系的结果,有些人表示完全没心情写,后来我才知道,好几位诗人有亲友在这次疫情中去世;还有的表示试一试;也有的立即答应,说除了写诗,也干不了别的……总之,各种情况都有。于是,初三开始,我们推出了“以诗抗疫”系列,后来还公开征集,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编了两本诗歌选。
“以诗抗疫”这个名称,是我定的,后来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质疑说诗歌能够抗疫吗?其实我是这样想的,维特根斯坦有过这么一个说法,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文字,文字是人之精神、文明的象征,诗歌作为最高最凝练的文字形式,标志着人之意志的昂扬,承载着人类精神的传扬。灾难之中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抗争,就是与病毒的斗争,证明人之精神没有垮掉。大疫之中,围城之中,武汉诗人仍在写诗,本身就透露很重要的信息,诗还存在,人还活着,人类之精神仍然高扬。
二
疫情期间,我也写了一些诗,第一首叫《来自珞珈山的春消息》,就是在约武汉诗人诗歌的时候,读到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的一首新作《庚子年初四,久雨初晴,以新冠肺疫,封城六日矣。》,诗曰:“一派晨光到眼浓,久阴喜沐乍晴风。聚街却任鸦闲步,闭户乃因市径封。疫疾遍传惟硕鼠,谣歌不听但佯聋。人间长幸是春色,已向梅枝暗现踪。”我读到的时候是初五晚上,读后感慨很多。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学生宿舍区都以花卉命名,“樱园”“桂园”“桃园”“梅园”等等,他写的显然是梅园景象,那里挨着图书馆。
第二天,初六一大早,我还在床上睡觉,听到窗外传来一声鸟鸣,恍惚以前在珞珈山读书时宿舍外传来的鸟鸣。去过珞珈山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学生宿舍几乎都在密林掩抑之中,我自己很早写过一首《珞珈山的鸟鸣》,说珞珈山是是鸟鸣的天地:“清晨鸟鸣啾啾,此起彼伏/正午鸟鸣交织,覆盖森林/黄昏,则只剩一两声鸟鸣悠然回响/你所能体验并有所领悟的最微妙境界/全在于你能否听得懂鸟鸣”,最后,对珞珈山的鸟鸣表示感谢:“就这样,当我还在懵懂无知的十七岁的时候/你给我启迪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我就想,也许这一声鸟鸣其实就是来自珞珈山上,穿越时空,抵达了我耳边。在一个新的特殊时刻,再次给我新的启迪。就这样,我起床写下了《来自珞珈山的春消息》,我在诗里写道:“春光乍现,将连日疫情中的阴沉武汉照亮/黄鹤楼、长江、东湖、龟山蛇山和磨山,还有/不时显现的一个个逆行的白衣天使的身影……/一一如此真切,如此美好明媚,在昏暗里闪过//是的,没有什么可以抵挡春天如期而至……/也没有什么可以封锁珞珈山上的一声鸟鸣/穿越千山万水,在晨曦微露之际/抵达自我隔离于海南岛上初醒的我的耳边”,倒不是说这首诗有多好,而是说诗歌的神秘在于其内在有着隐秘的一些联系与玄机。现在看起来,当时还是过于乐观了,武汉封城后来持续了好几个月,很多人的生活都因此发生了大的改变。

和著名作家韩少功在一起
我这期间写的几首诗,也都与读武汉诗友诗歌有关,引发种种联想。另外疫情期间,武汉大学读书期间的好友、珞珈诗派诗人洪烛的去世,也是特别让人伤感的一件事。我为洪烛写了一首诗《落樱》,诗里写道“春夜听到一个诗人悄然远去的消息/我默坐窗前,黯然神伤之际陡增白发”,确实,疫情使我们这一代人加速变老,白发陡增。洪烛是一个与所有人为善的人,所以朋友特别多。如果不是他去世,我还不知道那么多人惦念他。诗刊社微信发了一个他的去世消息,点击量竟然远超我们心目中的著名诗人,让很多人惊诧。
大学期间,我和洪烛、陈勇、黄斌等几个人经常在一起,有时甚至隔一两天就见,那时从来不谈论异性或八卦,只谈诗歌,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提出“珞珈诗派”,办各种诗歌活动,举办诗歌比赛,争相恐后发表作品,组织诗歌专辑。后来,隔了二十多年,竟然又在同一栋楼上班,还有邱华栋,我们楼上楼下,我们原来都在珞珈山上,现在又汇聚到了农展馆南里十号大楼,经常会在食堂遇见,然后坐在一起聊会天,真是一种很神奇的关系。我老是恍惚觉得我们还在珞珈山上,还是那群诗歌狂人,只关注天空、白云和清风。
洪烛之死,也让我意识到时间不等人,得抓紧行动起来,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一直认为:事情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我是一个行动派,一刻也闲不下来。要不就读和写。这,也许是一个诗人的宿命。
三
疫情期间,很多事情都停下来了,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诗歌活动不能举办,导致收入锐减。春节后除了刊物正常销售收入,几乎没有别的进账。《诗刊》是一个差额拨款单位,上面拨款只够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我有句口头禅:我们不能坐等,不能坐而待毙。我们要认清形势,主动出击。

虽然不能举办现场活动,但我们还是争取把《诗刊》的品牌效应扩大,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精心编辑,组织诗歌创作,我们这段时间主动向很多优秀诗人约稿,积蓄了一批好作品,将陆续推出;另外,根据上级安排组织了一些诗歌创作。我对诗歌一直强调现场性,所以三四月份重点推出了“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诗人”,最近,又将推出“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奋斗,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关键词,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破坏,奋斗尤其必要。这个编辑思路,我在《天涯》时就喜欢采用,我说我约稿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比如贾樟柯的《小武》出来了,其他杂志习惯约一些评论,而我会直接约贾樟柯写创作谈,所以那些年贾樟柯在《天涯》发了好几篇文章;二是与电影频道等举办了银屏“青春诗会”,因为这个活动开始没有什么经费来源,电影频道抱歉地说需要组织写一些特约诗歌,但没稿费,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就说这个费用《诗刊》来出吧。银屏“青春诗会”引起的巨大反响出乎意料,除了主题贴近社会热点,结合青春、春天来了、武汉解封和上万名90后白衣战士战役事迹,大量流量明星的加入,融媒体形式的采用等等,都加持了这一节目,五期节目全网观看量高达2、25亿次,相关微博话题浏览量高达35、77亿次,7次上微博热搜,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个活动也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惊奇,比如好几个合作主动找上了门,包括浙江温州一家文化公司提出联合开发衍生品等等;三是策划一些云上诗歌活动,开始尝试云上朗诵会和研讨会,我和《诗刊》的同仁们说,也许以前的工作模式会彻底改变,包括诗歌的传播方式,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也许,这个以后也许会成为常态,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习惯视频开会朗诵,虽然效果有待摸索;四是开发新业务,今年是中国诗歌网创办五周年,有一系列庆典活动,但都与新的业务开发有关,比如中国诗歌网准备开通抖音,开发电子诗集,建立中国电子诗集数据库。只有不断创新进取,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淘汰。
我们其实算是幸运的,我是一个一直有危机感的人,也许在海南那些年的起伏沉浮,让我知道各种情况都是会有风云变幻的,今年顺利不意味着明年也顺利,所以一定要抓住时机,能多做事多赚点钱,就先落袋为安。我们幸亏去年前年趁诗歌形势好,比较努力,账上存储了足够挺过难关的钱。要不今年这样开年还真是够呛,有可能就揭不开锅。
我是农村长大的,相信老人们一句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还有另外一句,则是很多智者常说的:生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自由,更别提什么发展。所以,首先是要活下来。
四
疫情期间,又认真地读了杜甫,再次关注杜甫。我一直喜欢杜甫,只要是关于杜甫的书,都会找来读。
这一次则与BBC播出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关。这个纪录片最早在一些英语专业网站和自媒体有介绍和评论,我看到后本能地觉得意义重大,就转给中国诗歌网的编辑,对照纪录片内容将其进行了综合,然后在中国诗歌网微信号和诗刊社微信号发布,仅仅两天阅读量就过了10+,其他一些网站阅读量也过了10+。我认为这个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与杜甫作为诗歌的标尺性人物,以及人们对他的爱国思想、人民性和悲悯情怀的广泛认同,包括当下特殊疫情有关。

这部片子其实有一个深厚的学术背景支撑,采用的基本素材、线索来自洪业非常著名的一本学术著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洪业早年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到哈佛大学做研究员,他这本书研究杜甫着力很深,所以这个纪录片在学术上没有什么硬伤,但纪录片毕竟是面向大众的,尤其是向不怎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读者做介绍,所以能拍到现在这个水平算不错了,整个格调是朴实的,里面不少当代图景也比较真实。
这部纪录片影响这么大,还是与杜甫的个人魅力有关。杜甫早年是一个强力诗人,“主体性”非常强大,在他历经艰难、视野宽广之后,他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了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所以历史称之为“诗圣”。杜甫让人感到世界的温暖和美好。比如他始终心忧天下,心系国家,社稷安危,百姓疾苦,在杜甫那里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即使他自己衣食无着朝不保夕。还有杜甫对儒家理想的坚持,任何困苦都不能阻拦他,他总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与乐观精神在跋涉前行,在寻找追求,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有杜甫的博爱与悲悯,他长时间颠沛流离,但仍关心比他更不幸的人,比如“安得广夏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等等……这些,都特别打动人。我看到电视里采访一个读者为什么喜爱杜甫,她回答说是杜甫在疫情中予人安慰。确实,读杜甫的诗,他的悲悯与同情心,让人感到来自历史深处的一种温情、博爱与力量。
这次疫情,更让人深刻感受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我觉得无论东西方,这个时候阅读杜甫,都会获得人性本身带来的温暖与安慰,唤起人类共同的情感,杜甫的伟大是超越时空与地域的。
五
疫情期间,让我感到安慰的一件事情是,根据我长诗《闯海歌》改变的戏剧《大海》,在一些可以称之为后浪的80后、90后中间不断引起一些涟漪和回响。
由于《大海》首演时正是去年年底,最忙的时候,我没法抽出时间回海口去海南大学现场观看,所以其实我对其效果是心里没底的。只是听很多师友反映不错,包括韩少功先生也给予高度评价,但我总觉得一些师友的夸赞可能是客气话,媒体反应也比较积极,可能是题材本身很传奇,表演方式很新奇吧。

李少君在朗读自己的作品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剧确实点燃了一些东西,尤其在莘莘学子们中间。大量年轻人参与了进去,比如在校学生演员,比如其全部音乐,是一个98年出生的北大学生吴宜瞳Yiti创作和制作的。她在今年四月份把这些作品放到网上,再次引起了反响。
《大海》网上音乐专辑的前言是这么写的:“大海的波涛从不曾休歇,与海有关的故事也总多波澜,环境剧场音乐话剧《大海》诞生于2019年末,并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20年1月初进行了第1轮正式首演。做戏的人,希望它像大海一样包裹着大家,让来到现场的观众们也的深深卷入其中。这部戏改编自李少君长诗《闯海歌》,导演邓菡彬则以九种情绪色调,重塑原著长诗中浮世绘般驳杂激荡的时代潮涌。同时邀请音乐人Yiti担任作曲和主唱,对应每场戏所需要的情绪状态,创作风格迥异的十首歌。《大海》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满怀理想的一代‘闯海人’为原型,将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涌浓缩在一个背着吉他走四方的主人公一系列故事之上。用音乐剧、话剧、相声剧、影戏、偶戏、舞蹈剧场、电影剧场等不同手法,从山歌小调到迷幻电子,流行摇滚到说唱的多元又统一的原创音乐,营造九个乐章的奇幻之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980年代已经过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传说,什么样的传说对于当代最有意义,这个才是重要的……李少君用他的语言进行了强烈的再创造,而我们则是用戏剧的语言进行强烈的再创造,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还原那种时代的丰富感。’ ”
专辑里有些歌词是我诗歌中的,有些是导演邓涵彬和人合作的,当然总体意思和我接近,比如有这么一段旁白:“楞头青、浑不怕,不伤感,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向外的力量,那是闯海人所共享的生命状态。演员们在场中时而化身时代列车铿锵有力,时而化身人潮滚滚歌声嘹亮。那个校园歌手,也边走边唱,看那大海上夜空中的白云飞扬,载着野心和理想。”于我心有戚戚然。
我其实是第一次听到这些音乐,说句很羞愧的话,那是一个晚上,夜深人静,我听着听着,居然流泪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想起了什么,也许是对青春的回忆,总之,很打动我,不同代人的那种激情、那种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吴宜瞳Yiti这个孩子很了不得,Yiti,吴宜瞳,1998年出生的新生代唱作人,1998年,Yiti生于东京,出生前家里已为她准备好了钢琴。在久石让、泽野弘之、管野洋子等作曲家及动漫影视配乐的影响下,11岁的yiti尝试用耳朵分辨并弹奏出记忆里的旋律,配上和弦,加上歌词,这就是最初的词曲创作。13岁开始学编曲,写歌逐渐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零碎的感受和想法都会化成一段段零散的demo保存在电脑里。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2018-2019年获北京大学十佳歌手冠军。2019年7月参与多媒体戏剧《庭石》的录制。2019年11月参演环境戏剧《大海》,并担任其原创音乐的创作及制作。
据媒体的报道:Yiti也拥有关于大海的独特情感,父母童年生活在海边,存在一种家庭中延续下来的、对海的亲切感。参与这部戏的创作之前,Yiti没有来过海南,“但过去之后就爱上了”。《大海》中多数音乐是到实地之后受到启发创作的,剧本后半部分还没有成型时,Yiti被邀到海南大学跟着排练,也得空四处转了转,“大部分的曲都是在那边偶然哼出来的”, Yiti将初来海南的兴奋与紧张,将陌生的海天与城市,将自己对海南的憧憬与现实的对照过程,谱成一曲曲或悠扬或激昂的旋律。对应《大海》这部剧采用的不同手法——音乐剧、话剧、相声剧、影戏、偶戏、舞蹈剧场、电影剧场等,Yiti因地制宜地打造出风格多元的音乐——从山歌小调到迷幻电子、再到流行摇滚、嘻哈说唱……《大海》的音乐创作极为成功,五一期间,海南音乐广播专门制作了《云上音乐剧——听<大海>》,每小时滚动播出系列线上节目,Yiti因此也重新制作了所有的音乐,每日一更,上线《大海》网易云音乐专辑……《大海》由诗而戏剧而音乐,又成功转化为了另一形式。内里的精神韵律却如波浪,不断翻滚,不断涌动,充满激情和生命力。
这一点,也让我看到了诗歌的无限可能性。我以前说过,诗歌有自己的生命,这一次真切感受到了。
六
疫情期间,我也思考来了对文学和诗歌未来的可能影响。我觉得,自然文学可能逐渐会成为文学的主流。
由于疫情,很长时间每天都几乎处于封闭隔离状态,每个人都赤裸裸地面对自然的生命生存状态。如此真实处境也让人思考。比如真切醒悟生活需要其实有时很简单,有方便面加一些配料就很满足了。五一在家时间比较长,加上北京市强调垃圾分类。突然发现,这真是一个让所有人面对自然的历史时刻。首先,你得了解垃圾,从何而来,又要如何分类处置,就需要了解每一样垃圾的特性,这真是比任何环保教育都能让人真正思索自然生态问题,万物如何产生,如何分解,如何循环。
疫情,使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越来越让人关注,这也许将成为自然诗歌和自然文学的新时代。这是我一直在思考并仍在继续思考的问题。生态意识、环保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逐渐成为新常态。

实际上,这一进程在敏感的诗人之中早已开始了。诗人沈苇,从空旷的新疆回到熙熙攘攘的杭州之后,转化为一个自然诗人,致力写作“植物诗”,宣称“每一种植物都是一个世界中心”;李元胜,走遍祖国大地名山大川,追踪研究花草昆虫已经很多年,在自然科普界声名赫赫,但他更在意寻觅“旷野的诗意”;雷平阳,一个以山水为寄托的诗人,誓言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他已经给好几座山写过传记;阿信的草原经验和草地诗学,在个别与普遍、世俗与神性建立起一种和谐的联系,堪称当代诗歌的一道景观。自然写作显然将越来越产生共鸣与影响。
爱默生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特别提倡自然文学,惠特曼和梭罗都是他的弟子,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庙里镌刻的一句格言。研习大自然,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终于醒目人类再也不能自大,不能自我中心主义,人不过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应该平等对待其他物种,与之和谐共存。
自然写作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和诗歌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比如古人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天地是一个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古人推己及人,由己及物,把山水、自然、万物当成朋友兄弟,王维诗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李白感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称:“水光山色与人亲”;辛弃疾则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世说新语》里记载:“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古人移情于物,更有甚者,忘情融物,物我合一,庄周化蝶就是例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一个大的境界中,心与天地合一,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人得以心安。
我对没有过自然生活经验的诗人,从来持怀疑态度,对于诗人来说,童年的经验极为重要,保存其最初的精神种子或者说初心,这是一些看似寻常普通的人最终成为诗人的奥秘。此外,自然是人类最早的家园,从小就受到大自然熏陶,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条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经验感受,确保了很多大诗人有更广阔的胸襟和包容的开放精神。
所以,自然写作,我理解就是要将自然理念通过文学作品和诗歌,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继而在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科学的环保的理念。在这一点上,诗歌从来在文学中有引领作用,也期望更多年轻的诗人加入这一行列。
垃圾分类,其实就是一门自然课,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全新改变。对于很多曾经忽视自然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端和起点。科学合理地处置垃圾,是人对自然负责任的一种方式。我们以前一味征服占有消费自然,现在则要开始节制,甚至考虑回报和补偿自然,如何遵循简朴的生活原则,如何更好地安置世间万物,包括垃圾,确保自然可持续发展。这样也使我们更真实地面对自我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让这个世界更加自然化也更加人性化,继而更加和谐美好。
-----------------------------------------------------------------------------------------------------------------------------------------------------------------

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大学期间参与发起“珞珈诗派”,1995年在海南发起成立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并任首任主席,2000年从《海南日报》社调入海南省作家协会工作。曾提出“草根性”诗学观点,引起广泛反响。主要著作有诗集《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神降临的小站》《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碧玉》(英文)、随笔集《文化的附加值》等,被誉为“自然诗人”。2003年至2011年任《天涯》杂志主编,期间策划发起一系列重要思想讨论。后任海南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首任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一级作家。